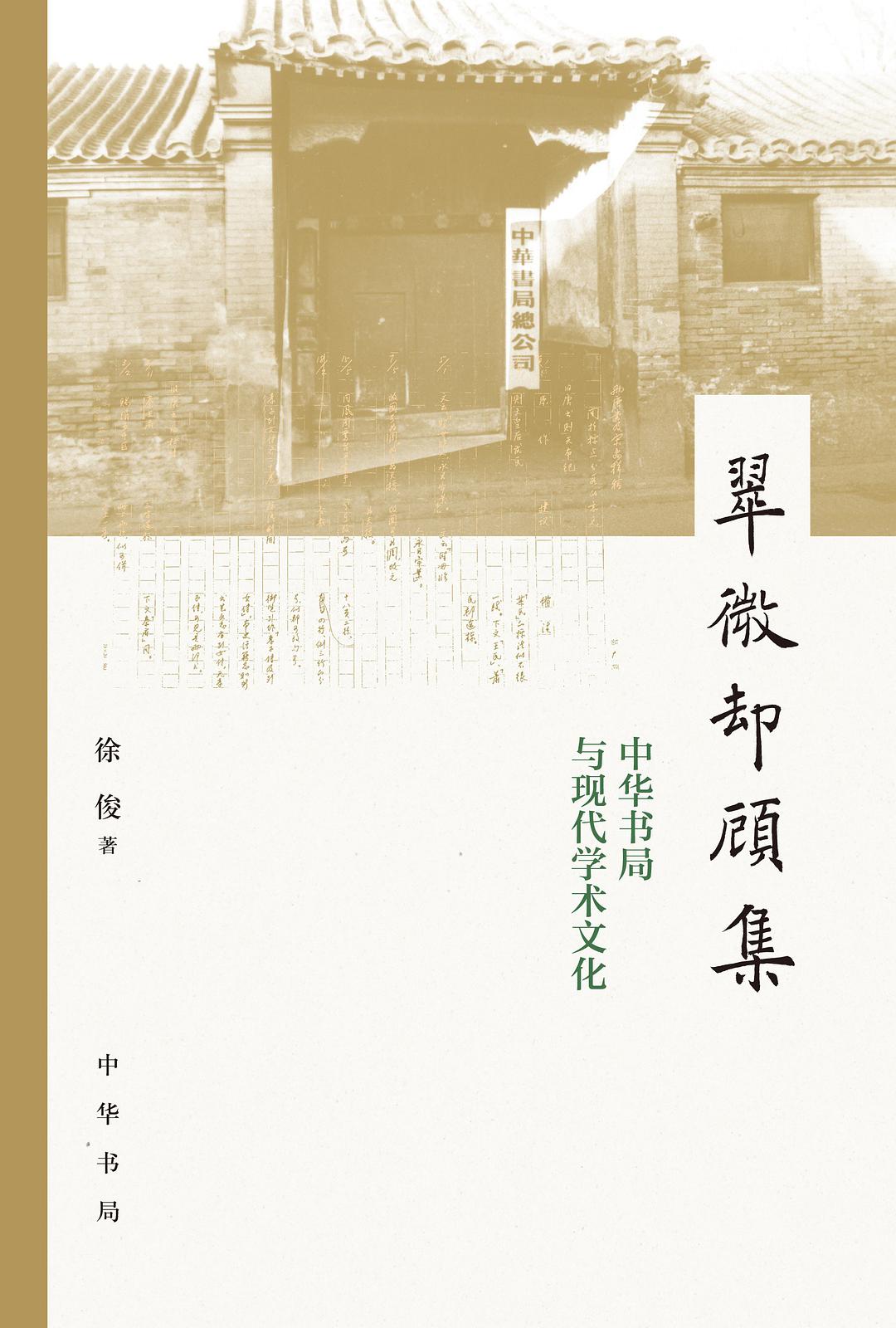
职业缘故,笔者特别被书中几位具有编辑人生的中华书局前辈所感动。
“‘二十四史’点校责任编辑第一人”:宋云彬
据《宋云彬日记》(中华书局2016年版),1958年2月,宋云彬拟《编纂〈史记集注〉计划(初稿)》,交当时浙江省委书记江华(28日),并寄友人征求意见(3月4、5日)。正如徐著所言:“正是这份《史记集注》计划,直接促成了宋云彬的进京。”当年7月11日,宋云彬先生的日记:“白(省统战部处长)谓中央统战部有信来,促余赴北京,有愈快愈好之语。问以要我赴北京作何事,则语焉不详,但谓据彼了解,恐系中华书局请参加整理古书工作。”9月13日,宋云彬先生迁京,15日即“赴中华书局看金灿然”,16日“上午七时一刻,赴中华书局上工”。徐俊对《宋云彬日记》及相关史料钩沉与梳理,让我们清晰了解到:“《史记》点校本成稿过程非常复杂,由贺次君初点,顾颉刚复点,宋云彬过录重点,聂崇岐外审,凝聚了四位先生的辛勤劳作和智慧学识。”这其中,徐俊对宋云彬先生的工作,更是着力用笔,提出了“‘二十四史’点校责任编辑第一人”,“我们从档案资料中,顾颉刚先生、王伯祥先生、宋云彬先生日记和书信中,去了解、理解他们所做的工作,宋云彬先生以右派分子的‘戴罪之身’每个月都要写思想汇报,检讨自己、改造自己,上午劈柴炼钢,下午晚上标点《史记》,一年的时间完成了《史记》的编辑和出版,其思想压力和工作强度可想而知”。《宋云彬日记》中,这样的记载还有很多,如:“下午政治学习。晚照例应学习历史,余仍标点《史记》”(1958年12月10日)、“下午奉陪开会,晚上补作标点《史记》工作”(1958年12月12日)、“星期应休息,但余照常点校《史记》”(1959年1月11日)等。自1959年4月完成《史记》点校后,日记中,又有许多看校样、勘误、点校《后汉书》,以及编辑《晋书》《南齐书》《陈书》《梁书》的记载,1960年5月26日,还写了一篇《关于〈史记〉标点错误的检讨》(见《宋云彬文集》第二卷,313页,中华书局2015年版),最后一条相关日记,是1966年5月5日,“上午照常工作,整理《梁书》校勘记”。此时政治形势日趋紧张,7月间即有《金灿然帮宋云彬搞反攻倒算》《宋云彬休想滑脱》等大字报(1966年8日、13日)。据宋云彬先生孙辈记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那年祖父69岁,‘摘帽右派’身份的祖父再次被批判、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身体和精神上所受的摧残,使他几乎崩溃。1966年8月一天的晚上,造反派到家里抄家,将书籍字画撕扯扔得满地,让两位老人跪搓板,冷热水交替冲头,说祖父是‘反动学术权威’、‘大右派’。”(宋京毅、宋京其《永远的怀念》,见《宋云彬日记》附录)《顾颉刚日记》(中华书局2011年版)也有相关记载:“宋云彬五七年定为右派,嗣后任中华书局编辑,未闻其有大过,而此次运动中,局方同人竟将其夫妇褫上下衣,痛打一次。”(1967年2月14日)其实,同年8月,顾颉刚先生也被贴出《把反动史学权威顾颉刚揪出来》大字报,“列诸罪状”,并“戴纸帽”,“拉入游行队伍”(《顾颉刚日记》1966年8月13、22日)。
由宋云彬先生日记,我们可知,自其1958年到中华书局,至1966年被剥夺工作权利,在不到十年的时间,为“二十四史”点校整理,工作到最后一刻,所以徐俊说:“称之‘二十四史’点校责任编辑第一人,当之无愧。”
“有着传统士大夫理想、修养和文人情怀”的“爱国民主人士、文史学家、编辑家”宋云彬先生,在生命的最后,躺在病榻上,跟家人说:“心中有三扇门紧闭着打不开”,并“带着这三扇打不开的门离开了”(见《永远的怀念》),不免让人唏嘘。
“一位不在编的临时编辑”:王仲闻
2009年,随着一部数十万字的《全宋词审稿笔记》出版,王仲闻先生的名字被大家关注,其对《全宋词》的贡献,由此被更多人所认识,有学者概括到:“细阅《笔记》,我们可以真切感受到王先生为《全宋词》所作的卓越贡献。这具体体现在对词作的辑补与校正、词人小传的补撰与修改、书稿内容体例的调整与编次等方面。”(潘明福《〈全宋词审稿笔记〉的学术价值》,《文学遗产》2011年第6期)王仲闻、唐圭璋两位先生对学术的执着与交往,为后来人所敬仰,如今已成为学术佳话。《笔记》书末,附有沈玉成先生《自称“宋朝人”的王仲闻先生》和作为《却顾集》开篇的《王仲闻:一位不应该被忘却的学者》,让我们对这位命运多舛的学人,以及其参与《全宋词》修订工作前前后后,有了更多了解,让几近被历史淹没的人,又回到了现实中来。
所幸的是时代在进步,沈玉成先生1986年的文章提出:“我愿意借这个机会,向中华书局诸执事提一个衷心的希望,王仲闻先生的署名当时既经商定,现在拨乱反正已近十年,以后如果重版《全宋词》,应该恢复这历史的真实。”又过了十多年,1999年,《全宋词》简体本出版,这个愿望得以实现。徐俊说:“这次简体本的署名,可以说是还了历史一个真实。”同时,他也提出了一个“私愿”:“但愿这份凝聚了王仲闻先生学识和劳动的珍贵的审读加工记录有机会整理出版。”徐俊的文章写于1999年,十年后,《全宋词审稿笔记》由中华书局出版。据悉,《王仲闻文存》也在整理之中。纸寿千年,王仲闻先生的名字不再会被遗忘。
“一生作嫁,却安之若素,甘之如饴”:周振甫
与前两位先生不同,周振甫先生二十一岁到开明书店做校对、七十八岁从中华书局退休,几乎一生从事编辑出版工作。《却顾集》收录有关周先生的文章四篇,“春雨润物细无声”,是徐俊的切身感受,“周先生是一个典型的谦谦君子,不善言辞,但和蔼可亲”。由于作者与周先生有同事和交往经历,文章所记,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往事,除了让人读来十分亲切,更能如同作者一样,感受到前辈“一种内在的职业品格”。
应该感谢徐俊整理这几份“审稿意见”,让钱、周交往,成为当代学术、出版史上珍贵的遗产档案。
读徐俊记录的这几段历史,我们能真切感受到老一辈学者对文化坚守的情结。像宋云彬、王仲闻、周振甫先生等许多老一代编辑、出版人,他们经历过时代风云动荡、政治格局变化、新旧文化碰撞,但无论处兴亡交替之际、命运顺逆之境,都能坦然处之,坚持做着为文化续命的工作,这一切,或许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已根植于他们的内心深处。
(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很多人按照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的标准,说他是法家学派弟子,也有人说他是兵家、墨家传人。那么诸葛亮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他究竟属于哪一学派呢?诸子百家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产物。此后,这些学派大多分流、演变。除了儒释道家思想活跃,其余的思想流派大多消隐。所以,三国时期人物诸葛亮的身上,并没有明确的思想流派...
在刺杀董卓失败后,曹操就开始起事了,仅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就统一了北方,甚至还挟天子以令诸侯。其当时所拥有的实力甚至是超越了孙刘双方的联盟。那么,曹操为什么会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呢?大多数人觉得跟曹操的奸诈有一定的关系,当然了,这兴许是一方面原因,当时最为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曹操的识人之明了。大家都知道,曹操...
第十名:步练师她是孙权的妃子,来自江苏,在孙权继位之后被封为了夫人,可以说是达到了皇后的地位,在步练师去世之后,被追封为了皇后,埋葬在蒋陵。第九名:祝融夫人她是三国里面唯一真正上过战场的女性,和孟获是一伙的,和孟获一起对抗蜀国的军队,在七擒七纵孟获之后,祝融夫人也归顺了蜀汉,据说他武艺高强,百发百中...
赵云,乃是继关羽、张飞之后,加入刘备集团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赵云算得上是蜀汉集团的元老级别人物。但是,刘备在称帝之后,给赵云的官职,仍然是一个“杂号将军”,赵云的权利,从本质上来说,没有丝毫的改变。很多人搞不明白,赵云前前后后,跟随刘备出生入死,差不多30个年头,为什么刘备就没有让赵云独当一面。给...
东汉末年,英雄辈出,谋臣如雨,武将如云。说起三国英雄们的武力值,这第一者当属吕布.随后才能够轮得上关羽、张飞等人.当时三个国家的实力都不容小觑,而大将最多者应...今天我们来看看三国时期的大狂人都是谁?Top8:虞翻虞翻是东吴的一员将领,虽然在三国时期他名声并不显赫,但他也是一位文武全才,尤其是他在...
果然司马懿跨渭河修桥,在两岸扎营,诸葛亮面对本想使用声东击西之策烧掉浮桥,却不想还是在司马懿刺探到了军情,溃败而返。第二回合司马懿想要反守为攻,将蜀军彻底围困,结果诸葛亮来了个埋伏战,扳回一局。等到第三回合,“木牛流马”这样在传说中流传了近2000年之久的“黑科技”除此登场了。本来是司马懿见蜀汉境内...
关家被害经过这一切,还得从蜀汉灭亡的前几个月说起。话说蜀汉末年,曹魏权臣司马昭派遣将领钟会、邓艾率领大军南征蜀汉。在古代,巴蜀地区是历代封建王朝都深感头疼的地方。因为交通因素以及统治技术的局限,一旦王朝出现衰败迹象,巴蜀地区往往会成为最先脱离朝廷统治的地区。并且,巴蜀地势的特殊,也让朝廷的讨伐变得收...
老刘没有发迹前只是家乡沛县的一个亭长,大致也就相当于乡科局干部吧?这个时候的老刘,那可真是本色毕露:不仅生性放纵好酒贪花经常戏弄手下的员工,而且还曾经多次出现过工作上的失误!多亏刘邦有几个好朋友帮衬——别人就不说了,县级干部萧何就多次替刘邦打过圆场,每次刘邦出现工作失误时,都是人家萧何替他周旋,这才...
熟悉三国的朋友,应该知道指的就是献帝刘协。事实上他之所以能够落得善终,与他一生充满了大智慧,是很有关系的。按理说他不是嫡子,皇位原本不是他的,再加上母亲也早早地被何皇后给毒死了。得知真相后的灵帝,尽管十分愤怒,但考虑到大将军何进,他也只好就此作罢。尽管何皇后如愿以偿地让自己的儿子刘辩继承了大统,但她...
比如此人的心肠异常的狠,不止一次地抛妻弃子,据正史的记载最少就有四次。其实这也算是一种无奈吧,无可厚非,因为在逃亡的过程中,带着家眷实属不便。这点倒是和他的老祖宗刘邦很像。当年刘邦兵败逃亡时,也是嫌马车太慢,好几次都把自己的两个孩子扔下去,都是夏侯婴又下去将其捡回来的,也正是因为这点,气得刘邦想杀了...
一日曹操不经意间看到儿子曹植的文章,连连点头,不时嘴角微微一笑。看完后不敢相信这是自己10岁儿子写的,问曹植:“你请人代写的吗?”,曹植胸有成竹的答到“话,说出口就是论;字,下笔就成文章,不信当面考考我就知道了,何必请人代写”。小时候的曹植性格坦诚,放荡不羁,不讲究仪表,车马服饰不张扬,没有官二代气...
这三次战役是公认的"三大战役"。不过以影响力来看,小编认为还有三场战役,其重要性并不亚于三国"三大战役",下面小编就来聊一聊这三次战役。小编认为"潼关之战"是一场很容易被忽略的重要战役,然而它对汉末三国时期的历史发展起到了很大的影响。我们知道"赤壁之战"失败后,曹操集团暂时失去了对南方扩张的条件,开...
这个无能主公不是别人,正是吕布。吕布,作为汉末一代诸侯,以勇武闻名,号称“飞将”,但是其政治思维偏弱,不善于利用自己的优势,导致一直被人利用,先是董卓,后是王允,最后又依附袁绍和张扬,偷袭曹操的兖州,窃取刘备的徐州,最终在徐州下邳之战中被曹操围困。这个时候,吕布麾下一位武将出场了,也正是今日小编要讲...
这位令人惋惜的女子就是汉昭帝的上官皇后,她也是霍光的外孙女,或许人们能够在电视剧中看见这个女子的身影。当时汉昭帝即位后,年龄仅仅只有8岁,由自己的姐姐鄂邑长公主抚养着长大。等到汉昭帝21岁的时候,鄂邑长公主开始为他挑选妻子,此时的上官氏也只有6岁。等到上官氏入宫之后,就被封为了婕妤,在此之后不久上官...
曹营救主斩杀曹军忠贞猛将总结赵子龙可能不是三国里最耀眼的,但他是最朴实的。朴实者,可以活得更久,这样的人无论在哪里都是令人敬佩信任的,因为他是贴近我们的,可以是我们行事的标杆。参考文献:《三国演义》《三国志》...
